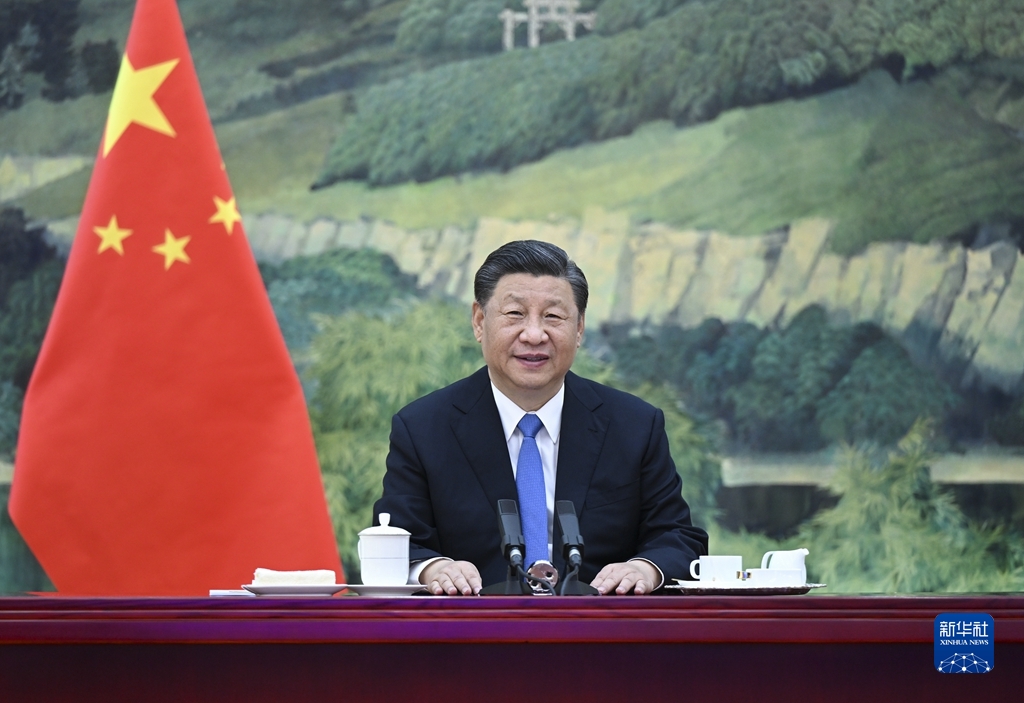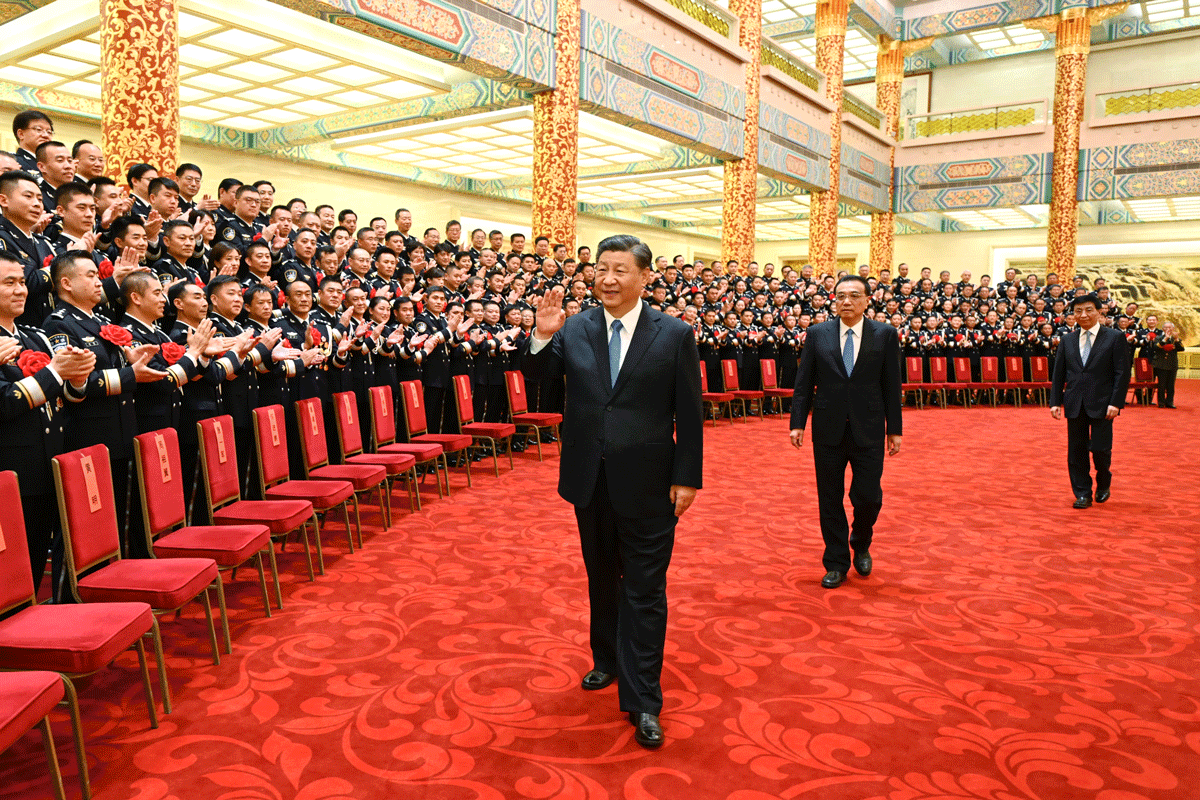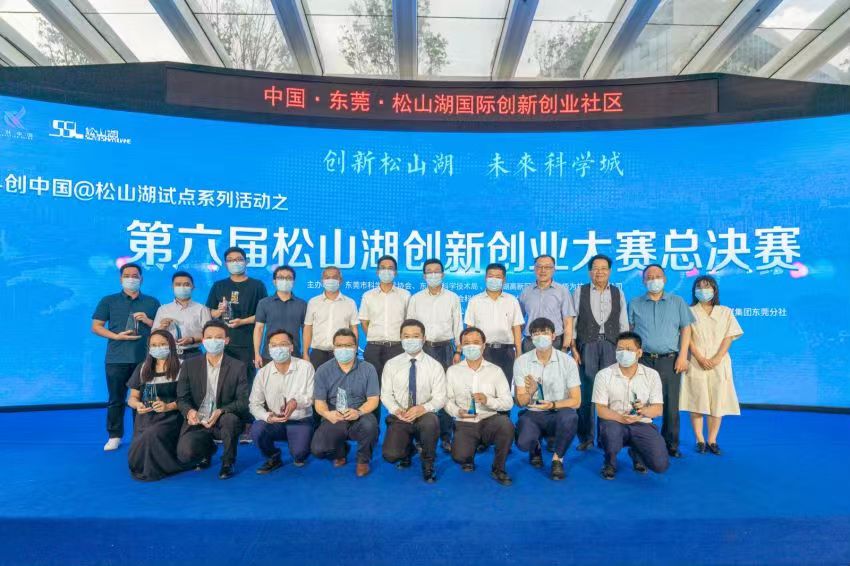澎湃新闻
新疆库车苏巴什佛寺遗址出土的7世纪彩绘舍利盒图像,以前多认为是“苏莫遮”欢庆乐舞,作者通过考证,认为并非如此,而是当时萨满教表演的巫舞巡回。
彩绘舍利盒图像充溢着浓浓的原始宗教气息,是龟兹当时流行的萨满巫术仪式在民间施法时的真实写照,也是佛教进入龟兹后融有原始萨满教的真实写照,透露出当时人们思想观念。通过对这件文物的再解读,文章恢复其那个时代本来的宗教面貌。
佛僧圆寂后盛放遗骨的舍利盒,不仅是佛教徒对高僧遗骨的礼拜,也是佛塔建筑内供奉的圣物。上个世纪以来,新疆地区于阗、喀什、龟兹、高昌等地多次发现彩绘舍利盒,日本、德国、法国等各国探险队屡次发掘获得至宝(图1/1~5),其中1903年日本大谷探险队在库车苏巴什发掘的唐代舍利盒最为精美,其精彩的乐舞艺术形象,一举成为举世瞩目的研究对象。
学术界一直认为将这件公元7世纪木胎大舍利盒定名为“乐舞舍利盒”,因为装饰彩绘画有戴面具的舞蹈图(图2),一些先生认为这是西域乐舞图,是龟兹乐舞唯一形象化见证,或是描绘龟兹假面舞“苏幕遮”演出的一个场面,手法相当写实。日本学者研究也是判定为古代歌舞戏的珍贵实物。
我观察思考很久,认为可能不是描绘欢快喜悦的乐舞,而实际很可能是萨满巫术巡回表演。作为一家之言,现提出来供大家聊备一说。
一 舍利盒被判定为“苏幕遮”乐舞场景的原因
库车苏巴什佛寺遗址出土的这件彩绘舍利盒高32.3厘米,直径37.7厘米,盒身周壁用布粘贴,布上绘有乐舞人物21人(图3/1~3)。盒盖上四个联珠纹圈内绘有四个跪姿奏乐带翼童子(图4~5)。被人们认为舍利盒周围绘一圈的是乐舞伎人,七个头戴面具的舞蹈者在翩翩起舞,除了男女持幡者,还有两个儿童抬着打鼓,最后又有两个击掌少年。
依据画面表现的乐舞,这件著名的舍利盒被学术界认为是“苏幕遮”,依据是史书对苏幕遮的记载,龟兹盛行佛教乐曲,《唐会要》记载有《龟兹佛曲》和《急龟兹佛曲》两大套曲,《羯鼓录》记载有俗曲《龟兹大武》,《酉阳杂俎》记载龟兹国“婆罗遮,并服狗头、猴面,男女无昼夜歌舞,八月十五日,行像及透索为戏”。有学者考证“婆罗遮应是娑摩遮之误,娑摩遮多译为苏莫遮”,龟兹八月十五行像庆贺,日夜歌舞和曲调总称为“苏莫遮”。但《隋书·音乐志》《旧唐书·音乐志》等官修史书记载过于简单,着重于乐器、曲名的记录,对乐舞表演的描述很少,只有佛教一些经籍较详,例如唐慧琳《一切经音义》四十:
苏幕遮,西戎胡语也,正云飒磨遮。此戏本出西龟兹国,至今尤有此曲,此国浑脱、大面、拨头之类也。或作兽面,或像鬼神,假作种种面具形状,以泥水霑洒行人,或持羂索,搭钩捉人为戏。每年七月初,公行此戏,七日乃停。土俗相传云:常以此法禳厌,驱趁罗刹恶鬼食啖人民之灾也。
慧琳的记载,解释了苏幕遮来自龟兹,其表演形式以假面、泼水相戏,主要形式以浑脱、大面、拨头为主,目的是禳灾驱灾。但语焉不详的是,这究竟是佛教传入的文化结果,还是龟兹本土原有的驱赶罗刹恶鬼?是戴面具化妆舞会还是来自异域的泼寒胡戏?“手持羂索搭钩捉人为戏”或许就是巫术施法表演的一种手段。
过去我们受唯物主义无神论影响,贬斥巫术表演为邪恶魔法的妖术,从意识形态上提炼舍利盒画面的主题,找寻相关的乐舞文献,似乎是文献与图像结合固化后铁板钉釘结论,所以对舍利盒多从欢庆舞蹈入手,描绘的喜气洋洋,载歌载舞,给人印象是舍利盒与丧葬无关,而是喜宴乐舞神话,回避了萨满巫术在当时的流行,省略了“此法禳厌”的最重要事实和驱鬼消灾的记录,不愿从萨满教巫师考虑,不愿触及禳灾驱鬼乐舞表现的本质。
我们始终没有疑问舍利盒彩画按照顺序排列,第一个人和第二个人为什么手持魂幡?苏幕遮舞蹈表演时需要持幡引导或高举扬幡吗?有人推测走在队伍最前面的两个人是一对青年男女,但他们手拿招魂幡,所起的引导作用不是一目了然了吗?舍利盒画面被误解美化为西域民族舞蹈,看不到巫术施法转圈过程与巫师跳神高潮的本身。
当然,造成最大误判的原因是“苏莫遮”传入内地后,逐渐由龟兹“土俗相传”的禳厌巫术乐舞变成了纯粹娱乐玩赏节目,到了中原唐中宗时期,长安改造原先裸体“泼胡寒戏”,将苏莫遮变为“夷邦归顺”的歌舞戏,甚至带有献忠祝寿、永庆万年的政治说教。据说苏莫遮泼水霑沥行人,原为波斯民俗供奉不死之神活动,清水象征“苏摩”圣水,具有“压阳气去病”禳厌消灾的意义。中亚康国到高昌“乞寒”“乞水”传播本意都是祈求天上之水滋润绿洲,但随着禳解仪式萨满巫师通灵呼唤降雨,集体欢悦与民间原始巫术紧密融合。
最值得指出的是,龟兹每年七月初举行的“苏莫遮”仪式,正是抗旱祈雨、禳病祛邪季节转换之时,而这些集体歌舞禳解仪式都是由声望极高的萨满巫师来主持,能够乞水(祈雨)、乞寒(祈雪)的萨满被赋予了连通神灵的功能,民间笃信只有萨满才能奏效。所以“苏莫遮”并不是佛教文化的产物,而是民间带有原始萨满的歌舞戏场面。
仔细观察舍利盒图像展开的长卷,现在解释为一个个被高度标签化的乐舞正面形象,但经不住推敲,可能离真实距离远了。宗教本身就会煽情造神,可艺术不会完全脱离现实生活本身,不会背离当时佛教的风俗习惯,这样的拔高主题与舍利盒彩绘图像相差甚远,如果舍利盒确实表现的苏莫遮乐舞,那么它演绎传达的可能就不是经历过生死轮回的再生,不是人们对死亡恐惧、敬畏神灵的过程,宗教历史就不是原初叙事而被不断改造重塑生成别的模样了。
二 舍利盒上乐舞应是镇魂与再生的巫术表演
我们注意到,舍利盒本身有着镇魂与再生的意义。镇魂就是告慰去世的亡灵,告慰死者的在天之灵,舍利盒的设计者和绘画者充分体现了这一理念,整个画面用长卷形式将现场变成了一个向神灵奉献神乐的表演空间,虽然没有表演神乐和舞蹈的场所,但是野外长队表演更使我们看到了萨满巫师巡游转圈的场景。在萨满文化影响下,人们认为舍利盒是安置死者肉身之地,同样承担了沟通生与死、连接地上和天上世界的功能,实则也可以理解为穹庐住宿、舞蹈音乐、绘画工艺等艺术形式的集合体,兼实用功能与艺术价值为一体。
舍利盒采用了圆堂祭奠亡灵的造型,象征着镇魂的文化内涵,营造的气氛就是跳大神的内敛气场,而不是热烈喜庆的气氛,这是我们观察时切入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纪念性的不是庆贺性的,气氛压抑不是兴高采烈。作为消灾祛病的祭奠性仪式,面临生死的考验。如果在丧葬追悼的情况下,人们还穿着华丽的盛装,粉墨登场,炫耀起舞,让丧家欣赏一场视觉盛宴的舞蹈,会激起什么样的反响,只会不受待见。
疏勒人慧琳法师记录的“苏幕遮”还可作为禳厌的面具,无论是凶煞的兽面,还是狰狞可怖的鬼神,都是由人扮作的,笔者曾指出龟兹舍利盒乐舞图中,“共有8个人脸戴假面具,其中4人戴尖耳噘嘴吐舌的野兽面具,另有4人戴嬉笑或长鼻哭丧的假面具,他们拉手拽扯跳跃起舞,并有11人乐队跟随演奏,前面还有两个长相端庄的胡人持节引导,应是一个完整的西域乐舞画面”。有学者也已经指出“西域面具起源很早,早期产生于狩猎生产和狩猎巫术,之后在广泛流行萨满教的西域,面具成了其沟通人神。祛病除邪。祈福禳灾的道具”。并分析萨满面具分为几类:狩猎面具,跳神面具、供奉面具,在祭祀、治病、追魂、驱邪、求子等仪式中运用,其功能有通灵媒介、神祇象征、隐己屏障、赐福灵物、护魂盔甲等,并在农耕与游牧生活中分野,西域不同区域面具功能有不同方式的差异。实际上,面具的多样化,正反映了除魔降妖、愁曲哀怨的多种形式。
西域禳灾驱魔的乐舞表演虽然不是阴森恐怖,但是在死亡的大背景下,还是对自身有着“克制”的文化现象,不能不顾忌他人的深深的悲痛情绪和巨大的悲伤心情。乐舞是有情绪的,西域本土的寓意值得玩味,他们并不求助精彩绝伦的盛会,而是禳厌消灾,或许舍利盒色彩黑红搭配寓意着痛失亲人的时刻,表示着血脉和肉体还能还魂再生。
我们看到舍利盒上巡游队伍前面七个戴面具人都是抬步跳起离地的状态,或单腿独立,或脚尖竖绷,萨满们跳的就是“痉挛”式舞蹈,在高抬腿舞步中表达肌肉神经和意识的混乱,是一种游离状态,似乎为梦游,又似乎为狂癫,舞者有种“鬼上身”不可理解的表现力。队伍后面的乐队有的人挥槌击鼓,有的人吹奏乐器,箜篌、排箫、阮咸齐上,特别是大鼓与鸡娄鼓占了二件,被描绘的非常雄硕,伴随着鼓点跳脚起步,转圈巡回不难想见,气氛高涨,紧张奇变(图6~1、图6~2)。
舍利盒绘画者将萨满巫师集体出动的场景,按照他们表演的动作分解成一个一个结构,然后按照前后逻辑拼接起来,试图表达一个祭奠神与人彼此沟通的理念(图7~1、图7~2)。遗憾的是,后人并不理解,忽略了这是禳厌驱邪的大场面,或许这个乐舞是为死去故人献上的丧葬之礼,阳间的人们看不懂也情有可原。我们不能把巫术舞蹈变成喜庆乐舞,就像不能把葬礼变成婚礼一样混淆。世界是个文化大圈,可是原始宗教的萨满遍及各地,我们尊重古人萨满的原创文化,试着解读其真实的哀思原意。
唐代段安节《乐府杂录》记载贞元年间长安大旱、设坛祈雨,西域琵琶第一高手康昆仑与伪装女郎的琵琶高手僧人段善本在长安“斗声乐”,作为祈神祭祀比胜负活动,并有女巫曾授“邪声”。这反映了唐人选择琵琶乐感天人、娱乐神人,在民间琵琶成为巫卜通灵器物,女巫通过琵琶占卜算命、招魂续命,男巫则以琵琶为法器行巫作法,为儿童、病人驱邪、招魂,形成了与娱乐演奏场合不一样的迎神活动,甚至分不清乐人舞蹈与巫觋跳神的区别,西域与中原这种民间乐舞融入了巫术的文化氛围之中。
实际上,中原内地在丧葬礼仪中,也使用丧乐挽歌,其歌声哀切,悲伤凄苦,最富情致,不仅朝廷大丧执绋扶柩歌之,而且贵族高官丧宴酒酣之后大唱挽歌。汉晋以后丧葬之礼,还用羽葆鼓吹作为对功爵勋臣的奖赏,丧乐由此大盛、风靡一时。尤其是,萨满类的巫术也糅合在丧仪中,驱鬼除妖的乐舞动作成为葬俗中的特色。有人说萨满教是古老的入迷术,就如祆教是萨满教在波斯环境下的变体,婆罗门教是萨满教在印度环境下的变体,儒教,也是萨满教在东亚环境下的一种变体。不管是否正确,至少值得我们思考古代萨满巫术的影响之大。
三 舍利盒反映了“巫医”与艺术治疗的现象
萨满教是数千年来活跃在北方游牧民族和绿洲农耕居民中的宗教,恶劣自然环境使得信仰者笃信世间万物灵魂的强大力量。萨满教在新疆地区出现很早,很多古代民族都信奉过萨满教, 有些地方曾十分盛行。专职祭司的萨满非常活跃,在突厥人、回鹘人等聚落中萨满享有很高的地位,他们不仅参与部族重要事务的决策,连行军打仗也要随行,他们参与军机并负责祈求神灵保佑军队打胜仗。在很多民族中,迄今还程度不同地保留着萨满教的习俗,如朝拜麻扎(显贵墓葬),在麻扎上插树枝、拴布条、持牛马尾,跳萨满舞等。巫术跟医学一样,都在帮助人们重拾生命的力量,拿回主导权,设法干预命运,协商社会关系,对社会和个人所面临的灾难不幸和困惑不安提出有意义的解释,对社会危机提供对策。
2003年在新疆吐鲁番洋海墓地发掘中,发现了青铜时代两座萨满巫师的墓葬,墓主穿戴特殊,耳戴金铜环,颈部玛瑙项链,靴系铜铃,体现了萨满巫师的装束,墓葬中不仅有巫师作法的道具,右手缠铜片马鞭,左手青铜斧头,还有致幻的大麻随葬,似为踏着鼓点节奏超度后的最终模样。这也证明草原游牧人三千多年来一直与萨满宗教文化传统相关连。
萨满就是巫师“跳大神的人”,即人和神之间沟通的使者。在科学不发达古代,萨满们通常扮演医生角色为人们解除病痛,被人们看作是先知、智者。他们穿着袍式神服,不仅色彩斑斓,而且在衣服上挂着兽皮、骨角等,象征万物有灵的信仰基础,一手手执圆鼓,一手拿着鼓槌或鼓鞭,有的就在神袍衣服皱褶里装饰红色的蛇形饰物,这是从“人”到“神”,进行身份转换的重要工具。
一个世纪以来,新疆发现的萨满教遗存证据很多,草原石人、墓地石人以及鹿石、岩画上都有表现,年代虽然有早有晚,但都与宗教信仰有关,延伸到欧亚草原上,游牧民族信仰的就是萨满教,各种怪诞奇异的神灵巫术被形象化于图像之中。小河墓地就存在着浓烈萨满崇拜的祭物,阿尔泰巴泽雷克发现服用大麻的铜锅,察吾乎墓地出土彩陶上神灵图案等等。
在萨满常见的服饰装束中,萨满头饰是标志性信物,有的头戴锯齿形铜质法冠,有的戴有高耸尖顶的皮帽。大多数萨满都要脸戴面具,或是头顶遮盖毛麻类饰物,女萨满戴的头冠还有常常的流苏,遮住大半脸庞,中国丝绸博物馆收藏展出的一顶流苏头饰(图8),可能就是萨满的头冠。1972年吐鲁番阿斯塔纳古墓群出土的唐代彩绘泥塑戴面具舞俑(图9),高32厘米,实际上也就是戴着面具做出仪式动作的萨满巫师。
民间萨满仪式通常与巫医正骨、外伤等治疗相结合,为患者解除思想恐慌包袱或是“驱逐恶鬼”。仪式通常从敲鼓环节开始,伴随着强劲鼓点和舞蹈,萨满们会进入恍惚状态,他们被祖先“灵魂附体”时会发狂,不断念念有词甚至口吐白沫,一个经典的萨满教仪式通常包括设坛、请神、献祭、驱魔、脱衣、颤抖、打滚等过程,伴随着大段的歌唱、舞蹈和咒语,有时仪式时间长达几个小时(时辰)。这种为了达到特定的驱魔祛病目的,鼓励信仰者笃信有自然界外精神力量的存在,人们要与它们保持互动关系就得尊重施展魔法仪式的“巫师”。
回头再审视龟兹舍利盒,图像中的导引魂幡、敲锣打鼓、歌唱舞蹈等一系列艺术的综合体巡回表演,就是一种满足人类心理需要的“仪式性行为”, 以艺术治疗的方法,“召回病人迷失的灵魂”, 萨满就成为沟通“从人到神”的重要角色,戴着虚假的面具起着驱鬼逐魔的作用,更有着神秘、霸气、恐吓的功能,发挥着常人所没有的作用。尤其是萨满以大麻、豪麻等植物为致幻剂,跳舞兴奋到疯癫以致扭曲产生幻觉,为深受生老病死种种疾病折磨的病人们寻求出神解脱之道。所以,萨满作为一个古老职业在游牧地区和阿尔泰语系地区非常兴盛,佛教等宗教在西域传播后,萨满地位开始下降,但萨满与佛教结合一起,不但没有消失,而且又渗入到新的宗教中找到了自己一席之地。他们不仅继续利用占卜、舞蹈等“魔法手艺”占据仪式主线,而且通过祖先传下来的娱神、降神、祈神、请神等仪式,用类似“艺术治疗”心理方式为民众打开心结。萨满教不绝如缕是生命力极强的宗教,以大众习俗的形式,顽强地生存下来。
遗憾的是,虽然匈奴、柔然、突厥、回鹘等新疆的许多古代民族,都信仰过萨满教。但是我国官方记载萨满巫师的历史文献在10世纪以前是极少的,有人将龟兹库木图拉石窟众神共舞的图像视作萨满教形象,恐不可靠。龟兹又是一个多种宗教杂汇地区,早期流行过原始萨满教,后来传来波斯祆教和摩尼教文化,占主流的大乘佛教中又夹杂小乘文化,此外藏传佛教文化、中原汉地传入的道教文化和净土宗、禅宗佛教文化都能从龟兹壁画中体现出来。源自萨满民间信仰的妖魔也摄纳入佛教信仰中的罗刹恶鬼,佛教借助萨满巫术“医病除鬼”成为宣传佛法能力无边的常见手段。具有宗教光环的僧侣群体和道士群体,他们渐渐成为巫术的主角。
阿克苏地区拜城县发现一处萨满教古墓葬群和占地一万多平方米的萨满教文化遗址,当时凡涉及本民族的重大问题和军事行动,首领都要事先由萨满占卜吉凶,征求神意,祈助神灵,然后才能决定行动。所以在这样的环境下,佛教遗址中出土的舍利盒上描绘有萨满教的仪式不足为奇。现在讲龟兹历史文化中佛教遗址、高僧、壁画、乐舞等内容很多,却回避萨满教的影响,这也可能是造成舍利盒被误以为是乐舞戏的一个原因吧。
萨满巫术是世界性的文化现象,近年学界相关研究成果甚多。狭义的萨满教特指以西伯利亚为中心,扩展到中亚、东北亚地区的萨满信仰;南方土著族群巫祝信仰也非常普遍,但均有舞蹈仪式为主导。广义的萨满乃是一种世界性的原始宗教现象。各个地域、各个民族之间的萨满文化虽有所不同,以“节奏性的鼓舞声音”使人进入“迷离”情景,可转化为宗教信仰生活中文化记忆,则在东西方历史上长久与其他宗教并存的。
中世纪尤其15—19世纪期间,西方将“巫师”“巫医”作为从事有害魔法的人,形成了对民间魔法师的敌意和憎恨,基督教认为女巫会利用咒语或仪式伤害周围人们,曾掀起了声势浩大的“猎巫”运动,特别是无数女性无辜者被描述成貌丑声诡、裸身狂欢的“女巫”,作为幽灵鬼怪的牺牲品葬身火海。直到现代许多国家巫术仍不断见诸报端。此外,中国巫师因拥有非物质文化遗产表演资格也是从事萨满职业的加分项。
总之,笔者认为库车出土的彩绘舍利盒图像透露出当时人们思想观念,充溢着浓浓的原始宗教气息,是当时7世纪萨满巫术表演时真实的写照,也是佛教进入龟兹后融有萨满教的真实写照。我们认真环顾一圈,画面是有先后秩序的,队列戴面具人物和乐队都是有血有肉的成员,反映着萨满狂癫和信仰者的热衷,所以我认为这是不能涂改或被掩盖巫术表演,我们不能选择性遗忘一些历史原始宗教的载体,通过对这件文物的再解读,恢复其其时代面貌。
2021年8月2日星期一修改于北京。
责编:翠果
责编:翠果
- 下一篇:一年一度的“正仓院展”,何以如见盛唐
- 上一篇:暂无